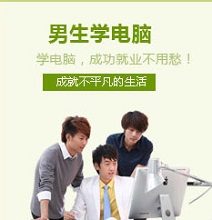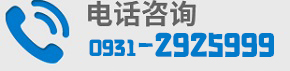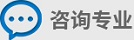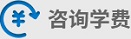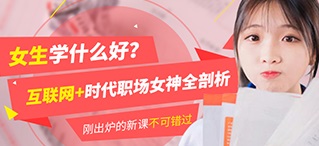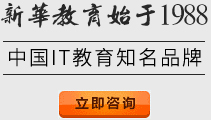在中國的教育版圖中,職業教育占有很大的比重,但一直都發展得不溫不火,關注度遠不及 K12 教育和高等教育,甚至被視為普通教育的「附屬品」。
2021 年 6 月,《職業教育法(修訂草案)》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草案中提到,「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是兩種不同教育類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明確了職業教育的法律地位。結合近幾年國家陸續打出的政策「組合拳」,職業教育的 「黃金時代」終于要來了嗎?
職業教育是國民教育體系和人力資源開發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官方定義,職業教育由職業學校教育和職業培訓兩部分組成。職業學校教育是學校教育的重要類型,分為中等、高等職業學校教育。職業培訓則包括就業前培訓、學徒培訓、在職培訓、再就業培訓、創業培訓及其他職業性培訓。
自 1996 年《職業教育法》頒布施行以來,中國已經建立起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職業教育體系。但種種時代背景之下,職業教育仍面臨著諸多困境和挑戰。
首先,在職業教育的體系建設上,政府雖然投入了大量資金,但各個地區發展不平衡、辦學條件參差不齊,教師、教材、教法體系建立還不完善。
再者,隨著我國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產業轉型升級不斷加快,我國對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更加旺盛。但蓬勃發展的新技術、新業態、新平臺背后,所蘊含的對產業應用型人才的巨大需求無法被滿足。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市場供需結構性矛盾突出,全國技能勞動者有 2 億多人,僅占就業人口總量的 26% ,而其中的高技能人才僅 5000 余萬人。
此外,高校畢業生數量持續增長,2021 屆高校畢業生規模 909 萬人再創新高,「學用脫節」導致大學生就業壓力日益增大。同時,傳統勞動力市場又面臨人工智能等技術的沖擊。一言以蔽之,職業教育仍是我國教育領域的短板。
近年來,為緩解市場就業壓力、實現高質量就業、順應終身學習的潮流,職業教育被寄予厚望,國家更陸續打出職業教育政策「組合拳」:2019 年,國務院出臺《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職教 20 條」);近期《職業教育法(修訂草案)》提請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審議,為職業教育的發展提供了政策和法律層面的支持;針對職業教育的細分領域,職教高考制度、「1+X」證書、產教融合、校企合作等支持舉措也陸續出臺。
政策東風之下,職業教育會迎來何種變化?
作為一種教育類型,學歷職業教育本應該形成自身縱向貫通的體系,為學生打通升學發展的通道,但社會上普遍對職業院校抱有「低人一等」的偏見。
而今,《職業教育法(修訂草案)》鄭重聲明,「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是兩種不同教育類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且為落實類型教育的定位,《職業教育法(修訂草案)》以「職業高等學校」替代原來「高等職業學校」的概念,對應于普通高等學校,包括專科、本科層次。這意味著職業高等教育未來將與普通高等教育「平起平坐」, 和普通高校一樣可以培養自己的本科生甚至研究生。
此外,今年 5 月公布的《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也明顯增加了多條關于職業教育的利好政策,如「實施職業教育的公辦學校可以吸引企業的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舉辦或者參與舉辦實施職業教育的營利性民辦學校」,「國家鼓勵企業以獨資、合資、合作等方式依法舉辦或者參與舉辦實施職業教育的民辦學校」,對實施國家認可的教育考試、職業資格考試和職業技能等級考試等考試的機構,此前《送審稿》中規定「不得舉辦與其所實施的考試相關的民辦學校」,在此次民促法新條例中則變更為「舉辦或者參與舉辦與其所實施的考試相關的民辦學校應當符合國家有關規定。」
但要真正鞏固學歷職業教育的地位,學校、專業、教師、生源缺一不可。「職教 20 條」明確提出,要開展本科層次職業教育試點,啟動實施中國特色高水平高等職業學校和專業建設計劃(「雙高計劃」),從院校和專業層面對職業教育進行了一波升級。師資保障層面,根據《深化新時代職業教育「雙師型」隊伍建設改革實施方案》,職業院校和應用型本科高校對專業教師的要求越來越高,要求任職老師起碼要具備 3 年以上行業企業工作經歷。
其實,自 2019 年以來,全國已經批準建立 27 所本科層次職業學校,這些學校主要由高職學校升格或是與獨立學院合并轉設而來,在培養模式、專業建設、課程結構、教師隊伍結構等方面都有別于普通本科。根據《本科層次職業學校設置標準(試行)》,本科層次職業學校的辦學條件包括師生比不低于 1:18、「雙師型教師」不低于 50%、2 個及以上校企合作項目等,標準可謂不低。這些學校的錄取分數線大都略高于本地本科二批分數線,對于提升生源質量、帶動整體就業層次均有著積極意義。
而中高職擴招、中考分流、職教高考則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職業教育生源的困境。自 1977 年恢復高考以來,每年 6 月的高考儼然成為我國最權威的人才選拔途徑。為打破高考「獨木橋」,構建人才選拔的「立交橋」,「文化素質+職業技能」模式的職教高考制度應運而生。今年 1 月,教育部與山東省政府出臺《關于整省推進提質培優建設職業教育創新發展高地的意見》,提出到 2022 年,「春季高考」將全面升級為「職教高考」,本科招生計劃預計將由現在的 1 萬人增加到 7 萬人左右。值得一提的,山東省職教高考報名對象為中職應屆畢業生和社會人員,不允許普通高中應屆畢業生參加,中職生的競爭壓力將會大幅降低,升學渠道一進暢通。
如今高等教育已經由精英教育演變到普及教育階段,為了不讓高等職業教育成為生源兜底者,今年 4 月 6 日,教育部發布《關于做好 2021 年中等職業學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提出「保持高中階段教育職普比大體相當」,職普比較低的地區要提高中等職業教育招生比例,對九年制義務教育之后的「分流」做出硬性規定。現在各地初三復讀政策已經收緊,中考失利的初中生不再允許在公立學校復讀,提前一個階段抑制普通高等教育規模「超載」。
為了提升競爭力和吸引力,職業教育既要有獨立于普通教育的辦學模式,也需要打通與其他類型教育之間的渠道。

在職普培養模式上,目前很多高職院校已經開始試水「高職本科一體化」人才培養模式。常見的有「3+2」(三年高職+兩年本科)模式和「3+4」(三年高職+四年本科)模式。吉林、江蘇、貴州等省份已經開始試點運行「3+3」模式,即學生在完成試點學校三年中專教育的基礎上,通過校內轉段升學考試進入高校接受全日制高職教育,畢業后發放普通高等教育畢業文憑。河南省也將支持專科高等職業學校與應用型本科高校、本科層次職業學校開展「3+2」對口貫通培養試點。
在職普待遇平等問題上,《職業教育提質培優行動計劃(2020—2023年)》明確提出,推動各地落實職業學校畢業生在落戶、就業、參加機關事業單位招聘、職稱評審、職級晉升等方面與普通高校畢業生享受同等待遇。不過,按照目前學歷文憑在就業市場越來越「內卷」的趨勢,能否在上述各個方面實現待遇平等仍需要畫上一個問號。
職業教育外部依賴性高,需要主動與社會、行業、企業實現跨界融合,但目前職業學校與企業的合作協同度還不夠,常常是職業學校「一頭熱」,企業和行業協會參與積極性不高,課程缺乏靈活性和前沿性,「產教分離」現象較為明顯。要實現職業教育現代化,職業院校必須了解企業需求,提升產教融合轉化率,否則培養出來的人才就是「無源之水」。
近幾年,「產教融合」在國家政策中被反復提及。2017 年底,首次從國務院層面出臺深化產教融合文件,「職教 20 條」、修訂草案也均包含產教融合和校企合作、支持社會力量舉辦職業學校等相關內容。2019 年《國家產教融合建設試點實施方案》提出,5 年試點布局 50 個左右產教融合型城市,在全國建設培育 1 萬家以上的產教融合型企業。今年國家發展改革委明確對認證產教融合型企業給予「金融+財政+土地+信用」的組合式激勵。截至 2020 年,全國已經培育了 800 多家產教融合型企業,成立 1500 個職業教育集團,3 萬多家企業參與職業教育。